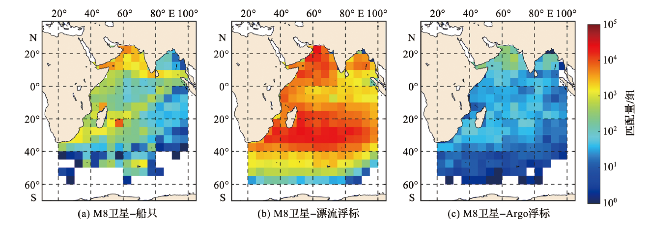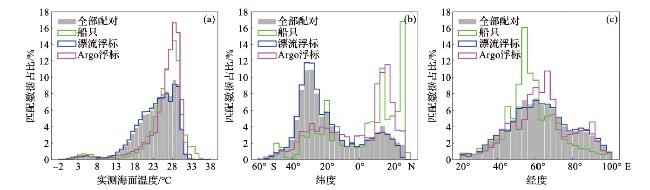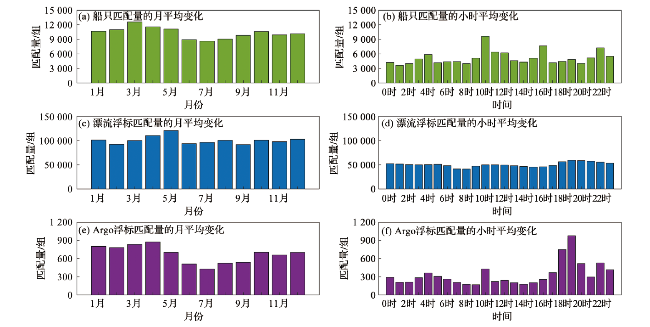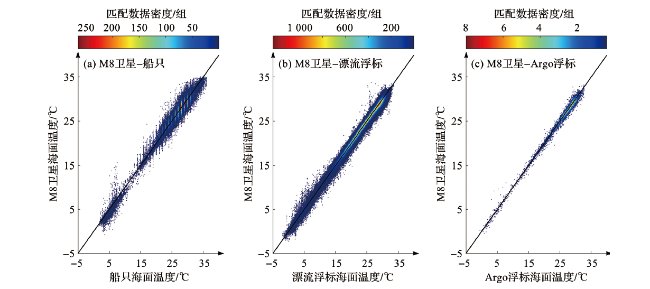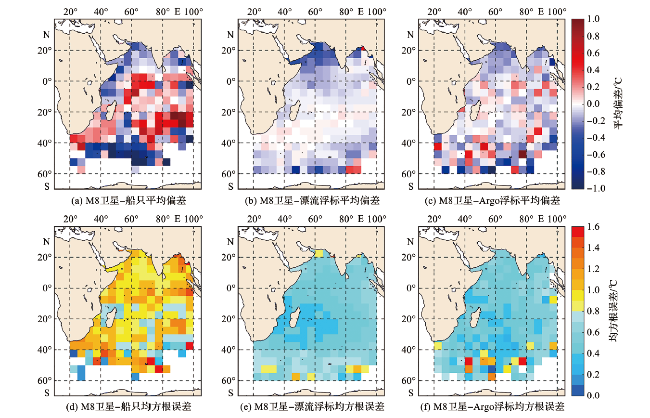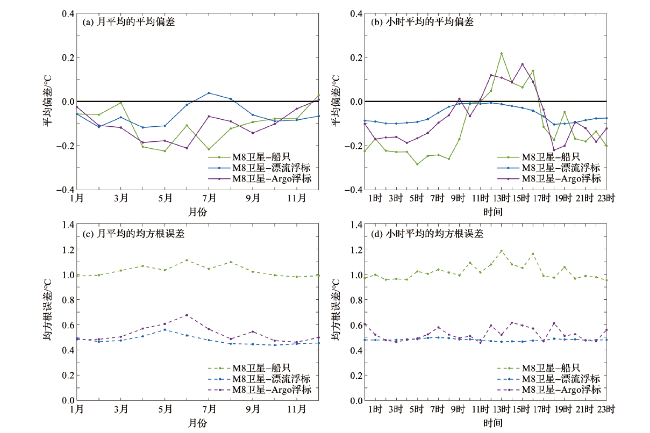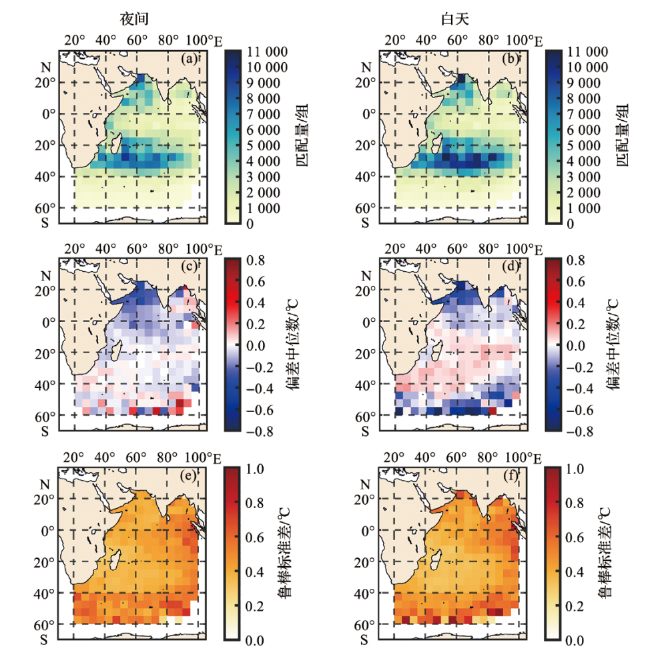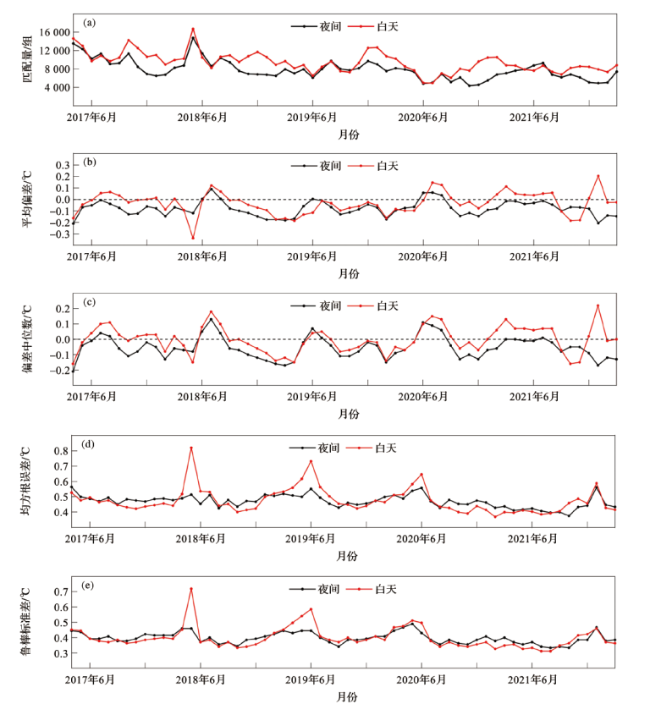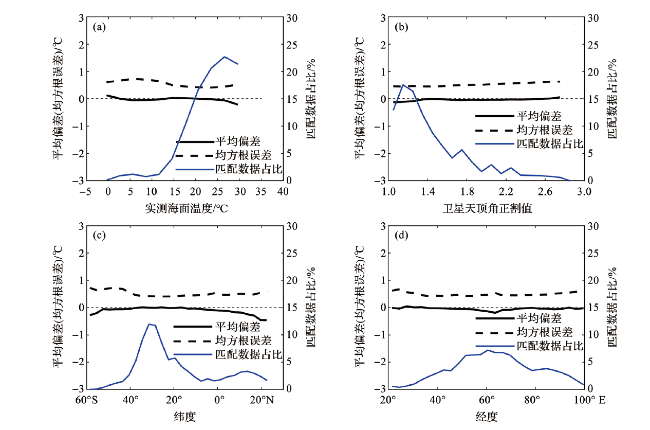0 引言
1 数据与方法
1.1 数据来源
1.1.1 M8卫星海面温度数据
1.1.2 实测数据
1.2 研究方法
1.2.1 M8卫星海面温度反演算法
1.2.2 匹配方法
2 M8卫星与实测平台数据的匹配特征
图2 M8卫星与三种实测数据的海面温度(a)、纬度(b)和经度(c)匹配情况分布直方图(海面温度分组间隔为1 ℃,纬度和经度分组间隔为3°,直方图归一化积分为1。) Fig.2 Histograms of SST (a), latitude (b) and longitude (c) distributions for paired M8 and three in-situ platforms (Grouped by 1 ℃ for SST and 3° for latitude and longitude,histograms normalized to a sum of 1.) |
3 M8卫星数据与实测数据误差分析
3.1 整体误差统计
表1 M8卫星与三种实测海面温度数据的误差统计表Tab.1 Statistical table of SST errors between M8 and three in-situ platforms |
| 实测平台 | 匹配量/组 | 平均偏差/℃ | 均方根误差/℃ | 决定系数 |
|---|---|---|---|---|
| 船只 | 124 089 | -0.10 | 1.03 | 0.96 |
| 漂流浮标 | 1 208 438 | -0.06 | 0.48 | 0.99 |
| Argo浮标 | 8 067 | -0.10 | 0.53 | 0.99 |
3.2 误差的空间分布
3.3 误差的时间分布
3.4 M8卫星夜间与白天海面温度验证
表2 M8卫星与漂流浮标夜间和白天海面温度误差统计Tab.2 Statistics of SST errors between M8 and drifting buoys for night and day |
| 时段 | 匹配量/组 | 平均偏差/℃ | 偏差中位数/℃ | 均方根误差/℃ | 鲁棒标准差/℃ |
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
| 夜间 | 470 166 | -0.08 | -0.05 | 0.47 | 0.41 |
| 白天 | 566 952 | -0.04 | 0.00 | 0.48 | 0.40 |